
黑人反思铃钩和她的作品
感谢bell hooks -来自黑人
的一个基石贝尔挂钩的工作父权观念对男人和女人都有害。在她2004年的书中《改变的意志:男人、男子气概和爱》,胡克斯指出,社会对男子气概的期望会对男孩产生痛苦的影响:“为了向男孩灌输父权制的规则,我们迫使他们感受痛苦,并否认自己的感受。”为了实现性别歧视的理想,胡克斯指出,男孩会因“灵魂谋杀行为”而得到奖励。
更直接地说到黑人的困境我们真的很酷:黑人和男子气概,胡克研究了种族主义是如何帮助形成对黑人男性的社会期望的:“在新殖民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中,黑人男性的身体继续被视为兽性、暴力、阴茎作为武器的超男性主张的化身。”她哀叹,作为白人至上主义社会中的黑人,我们被教导要把躲避脆弱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也就是说,因为这使我们远离爱。
胡克长期以来一直支持黑人男性的温柔和自由的能力。我亲眼目睹了她对它们的痛苦和珍贵的认可。当我们继续纪念她的生活和工作时,我认为黑人男性应该在她的脚前献上玫瑰。

当我们能看到真实的自己并接受自己时,我们就为自爱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 - - - -贝尔钩
谁没有被贝尔改善?让你流泪,带到井边,让你喝?贝尔·胡克斯本身就是一门完整的语言。我第一次读她的作品时,不仅要重读她的作品,还要重读自己的作品;重新认识和忘却我自己和男子气概的含义。我们执着于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贝尔教我们如何避免在父权制的伪装下受苦,以一种可怕的治愈方式,与一种美捆绑在一起,而这种美并不受制于白人女权主义作为我们看待自己的镜头。贝尔不是用来玩的。贝尔解放了我们所有人。贝尔为我们所有人活着。
当我想到贝尔的时候,我也会想到托妮·莫里森;我也想到了安吉拉·戴维斯。我想起了为我们遮风挡雨、扛起重担的黑人妇女。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当我想到钟钩时,我想到的是午睡牧师的崔西娅·赫西休息和恢复的想法;所欠的赔款,以及作为一个黑人女性在美国所付出的精神、身体和精神代价。一个女人的工作,一个黑人女人的价值,是如何与我们看待自己的散居方式紧密相连的:在每一个字,一本书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个大陆屈从于殖民主义的冲动中,我们也能看到那座钟呼唤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在钟钩上,我们可以看到通往解放的道路是如此清晰、干净、赤裸地为我们铺就。
我一想到贝尔就想到奥德丽Lorde;我想到了索尼娅·桑切斯和尼基·乔瓦尼。我想到了格里奥和作家的血统,他们巧妙地向我们讲述了自己。我想到他们给了我们机会去见证那些暴露的伤口。我想起了Kimberlé克伦肖的艾达·b·威尔斯,想起了凯瑟琳·克利弗;我想到黑人女性与传统格格不入,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质疑黑人身份的方式和原因,以及这种经历的全部,以及它是如何在白人世界的背景下出现的,而白人世界宁愿看到我们受苦,也不愿看到我们奋斗。我的朋友左拉艾伦谈到世界建设:我们可以创造这些生态系统,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自由。贝尔·胡克斯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星球——一个哺养我们、解放我们、给我们光明和爱的人,以及我们需要的那种混乱的介于两者之间的人。
当我想到铃铛钩时,我想到的是爱——一种撕心裂肺、惊心动魄、让人畏缩的爱。这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爱可以改写、重塑和重新审视一个民族的历史……我们的人民。当我想到铃铛钩时,我就想到一面正正确地朝着更美好的未来的镜子,一面相互支撑的镜子,一种我们将花费数年时间来拆解的语言的反映。铃铛钩让我们在表达黑人和爱时感到自由,以一种既令人愉快又鼓舞人心的方式改变权力动态。贝尔从不迎合,从不畏缩。贝尔从未让我们觉得自己渺小。我们比白人因为贝尔想给我们的任何部分的总和都要伟大。因为贝尔,我们成为了巨人。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人民——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因为贝尔而变得更好,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后的每一天。——乔尔·莱昂“当我想到铃铛钩时,我想到的是爱——一种撕心裂肺、惊心动魄、令人压抑的爱。”——乔尔·莱昂

我第一次接触贝尔·胡克斯是在2011年秋天的一门女权主义法学课程上.我在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攻读法律硕士课程期间,研究性别与法律,安·沙莱克(Ann Shalleck)教授想要挑战我和我的同事们对女权主义的看法,即女权主义理论只适用于富有的白人女性。从让我们读书开始《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和《女权主义为所有人:激情政治》变成了我毕生致力于胡克斯的工作,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并寻求关于种族、性别、性、阶级和社会经济学的艰难问题的真相。
在我的学习中,以及后来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勾子成为了一个完美的例子,是我们许多人的北极星,说明了把最边缘的社区集中起来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种做法在倡导工作中非常重要。即使是在致力于学术的时候,胡克也深深明白,绝大多数需要关于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的信息的人并不总是(或通常)在学术领域。在她的作品中,胡克斯让所有人都能接触到女权主义,并努力颠覆它,让它不再是只有白人女性才能接触到的东西。
在她的写作和演讲中,胡克让我们沉浸在希望和爱中——并迫使我们认识到,这些行为也同样激进。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一点是在她2000年的开创性著作中关于爱的一切:新视野,在那里,钩子挑战了我们的日常观念,即给予和接受爱意味着什么,以及现实是如何被扭曲的,往往是由我们的青春期早期塑造的。从那以后,它让我反复学习关心、承诺、同情、开放的沟通和脆弱。相反,它迫使我去思考忘记父权制和操纵。
作为一名黑人酷儿,我从未像在她2003年的书中那样感受到与钩子更深的联系,我们真的很酷:黑人和男子气概.在书中,她写道:“在男权文化中,所有男性都学会了一个约束和限制自己的角色。当种族和阶级与父权制一起进入画面时,[B]缺乏的男性忍受着性别化的男性父权身份的最恶劣的强加。”对于胡克斯,她知道在一个以白人为中心和白人至上的美国,许多黑人男性被迫压抑自己。如果再加上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态度,黑人男性,尤其是那些愿意颠覆这些制度的人,就会被定罪,失去人性。
69岁是年轻的。我们的长辈在这个年纪做祖先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胡克必须休息,就让它完全平静地休息吧,要明白我们确实关注的是她的工作内容,而不是她是谁——尽管这碰巧也令人难以置信。- - - - - -普雷斯顿·d·米彻姆先生,。
“她给我和像我这样的男人和男孩写信,明白无论好坏,卑鄙的父权制的管理权都在我们手中。”安德鲁-特

纪念贝尔·胡克斯的正确方式是去爱得更好。但现在,这种爱的主要例子——她对教学无休止的身体投入、她洪亮的声音、她滔滔不绝的话语——已经离开了物质世界。所以我必须引用她。在这些关于我们的希望和梦想的说法中,我必须引用她的“祖先”。正是因为有了她,我们现在才把父母和看护人的无意识任务称为“情感劳动”。她是我们对资本主义新流行的批评的来源,我们以更深、更人道的爱的名义,站在反抗和怀疑的立场上。一份没有华丽价签的爱。她让我们明白休息就是爱。我们不能因为她的工作成果无处不在,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就忘记她。我不能忘记,现在是我贯彻这些原则的时候了,这样她也能最终得到休息。
但如果我说我支持爱而不是暴力,那就是在撒谎。在表现爱的行为和破坏爱的行为之间的那条界线,也是把男人和我们虐待的对象区分开来的原因。我仍然经常暴力、虐待和冷漠。也许不是因为贝尔·胡克斯的作品再说一次我爱你.她写信给我和像我这样的男人和男孩,明白无论好坏,卑鄙的父权制的管理权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她明白我们宁愿内爆也不愿放弃控制的想法。这就是她所面对的。
我要在这里引用她,向我生命中那些我说我爱,我想爱的女人宣誓,但她们没有得到贝尔·胡克斯教给她们的足够或任何人道的奉献。2006年,在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一次演讲中,她明确表示:
“每个女人都想被男人爱。每个女人都想爱和被她生命中的男性所爱。无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双性恋还是独身者,她都想感受来自父亲、祖父、叔叔、男性伴侣或儿子的爱。想想那些有儿子的女同性恋。他们希望孩子是他们可以从童年到成年都爱的男性。在我们生活的文化中,情感匮乏、被剥夺的女性拼命地寻求男性的爱。”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母亲渴望我更多的爱。我让她独自哀悼她的亡夫,亡父,亡叔。我的阿姨们一直在忍受着情感上的劳动,而我家里的男人,可以预见的,死去了,消失了——他们的爱的痕迹在任何人还没能抓住之前就消失了。必威betway安卓app当我写作时,我知道我的浪漫爱情渴望我更多的承诺。不仅仅是在枕边闲聊和庆祝的时候,而是在艰难和愤怒的时候,在我被忽视的痛苦时刻。因此,我正在重申我对一种倾听的爱、一种顺从的爱、一种围绕着一个社区并在其中塑造自己的爱的承诺。我重新承诺我最好的老师,知道她的名字是她留下的充满爱的实践的代名词。安德鲁-特
钩子成为了一个完美的例子,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一颗北极星,说明了什么是最边缘的社区的中心…”- - -普雷斯顿·d·米彻姆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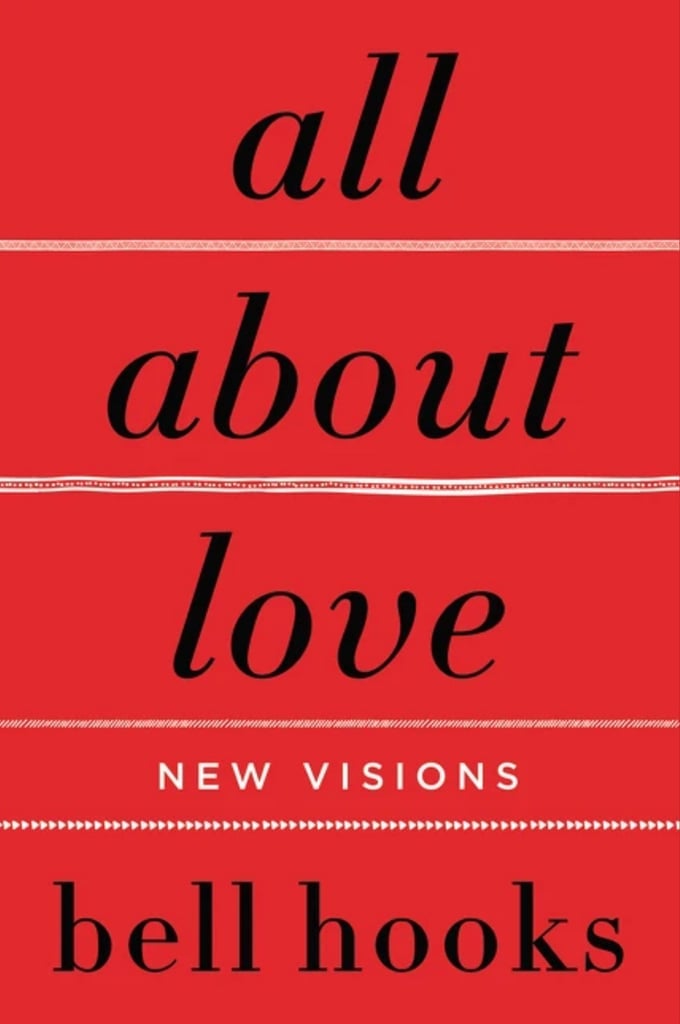
我走进贝尔·胡克斯的餐厅再说一次我爱你在结束了为医疗工作者工会举办的八个月的以大流行为主题的虚拟悲伤和失去研讨会的第二天。
我一直背负着数百个毁灭性的失落故事,我试图说服自己“只是信息”。直到妈妈提醒我那些故事对我的身体和精神产生了影响,我才开始意识到它们对我的影响。我在布鲁克林的第一间单人公寓住了10个月,在经历了多年糟糕的心理健康状况、无家可归和残酷的非人性化之后,我努力重建和爱自己。
我经常感到麻木,与自己的情感脱节,但当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用她对年轻一代的恐惧来唱我的生活时,她让我以新布道者的热情发短信、贴出节选,因为年轻一代追求的是没有亲密关系的快乐,“如此害怕失望的痛苦,以至于他们将放弃爱和快乐的可能性”。
第二天晚上,我大口喘气,在书的前几章做了标记和注释再说一次我爱你在我的门廊上,我打电话给几个身处不被人刺伤的工会的聪明朋友,问他们一些问题,比如“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恋爱了的?”“你是怎么了解爱情的?”“好吧,是啊,但是,是怎么知道的?感觉像吗?”
我阅读了胡克斯的作品,写了一页又一页充满激情的、有标题和插图的日志、彩色高亮和投票记录。回想起来,我是一个被爱着的人,但被恐惧、羞耻和无法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的回报所束缚。当贝尔转向自爱的基础时,我感到既被关心又被攻击。我试图给予和接受爱的努力被我那破烂的自尊所中和,它被用下划线、粗体字和斜体字标出。
铃铛钩揭示了未愈合的伤口、熄灭的激情以及爱与无爱的舞蹈是如何塑造、着色、加深、维持和缓解我们的痛苦的.当她向我解释“我们受伤的程度经常导致心脏关闭”时,我感到充满希望。她充满爱意地告诫人们,不要指望别人给予你的爱来填补你的裂缝,并指出,认识和命名事物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在主持了一个关于悲伤的文学治疗写作会议并能够评估创伤后成长的第二天,我读了她关于社区的章节。我合上书,绕着街区走了一圈,贝尔提醒我:“我们很少——如果有的话——能在孤立中痊愈。”治疗是一种交融的行为。”我没有意识到,在那些空间里的友谊、安全以及受欢迎的脆弱对我自己的恩典有多么重要,而不是让我凶残的内心仇恨占上风。我需要那种哭泣。
在这个巨大的损失之后,当悲伤蔓延,感激之情倾泻而出,看到这个天才拯救了多少人,并在她的照顾下获得自由,我感到安慰,让我记住,虐待不能与爱共存,并欣赏我们自己的所有部分,而不管世界如何回应。
谢谢你,贝尔。——亚历山大·哈代